亚当·图兹:《哈耶克的私生子》——中国、美国与可持续发展
新右翼的本土主义与种族主义并非与新自由主义水火不容,而恰恰是从新自由主义内部孕育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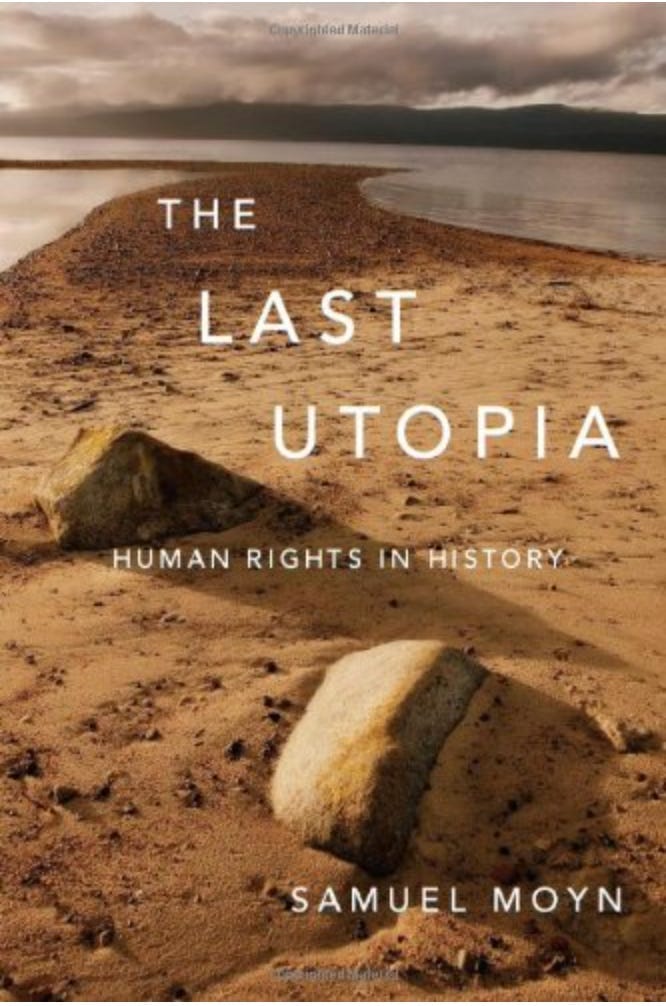
【编者按】欢迎来到「图说政经Chartbook」。这里是由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主理的Chartbook的中文版,经图兹教授本人授权。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协定》的出台堪称全球治理高光时刻;而今回首,那却是“最后的乌托邦”时刻。随着美国右翼主权主义回潮,美国声称上述议程威胁自身主权与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话语中成为了2015年秩序的最大守护者,全球治理的坐标系在悄然重绘。
本文英文版发布于2025年9月12日。
作者:亚当·图兹
译者:包岳涵江
责任编辑:高铂宁
2015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就在十年前的这个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随后在12月又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那是一次围绕普世主义目标而形成合流的独特时刻,也是改革式的“全球治理”的高光时刻。用一个我们稍后还会回到的说法,那是一个“最后的乌托邦”的时刻。
十年之后的2025年3月,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在联合国亮相,以极其激烈的措辞抨击了这些协议。
以下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会上宣读的文本:
尽管措辞看似中立,“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推进的是一种与美国主权不相容、且不利于美国人民权利和利益的软性全球治理方案。
美国选民在上一届选举中已发出明确指令:政府必须将美国置于首位,首要关切本国人民福祉。我们必须首先、并且最重要地关切本国公民——这是我们的道德与公民义务。特朗普总统还对贯穿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性别”和气候意识形态作出了迟来却明确的纠偏。
简单来说,像“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类全球主义举措在选举中被否决了。因此,美利坚合众国拒绝并谴责《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且今后不再例行重申它们。
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讨论过美国政府这番不同寻常的谴责性言辞。
亚当·图兹:为什么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摒弃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却无人察觉?
我们该如何解释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右翼“主权主义”的回潮?
一种可能的解读路径来自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新书《哈耶克的私生子》(Hayek’s Bastards),该书在四月中旬上述文章发布后仅数日即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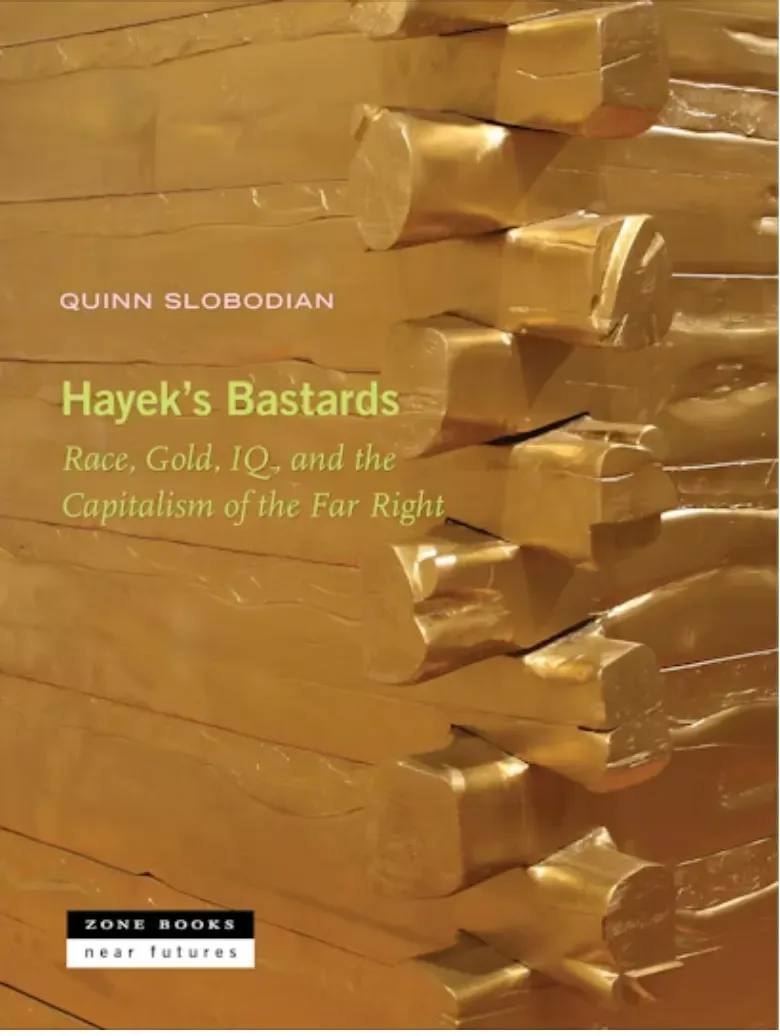
一如既往,斯洛博迪安带我们展开一场对右翼心智的引人入胜的巡游。但在我看来,他的分析真正扣人心弦之处在于其背后的那个更宏大的设问: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西方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新自由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
人们或许会认为,那是新自由主义最为辉煌的时刻。毕竟,“华盛顿共识”这一提法出自20世纪90年代。可正如斯洛博迪安所指出的,至少对新自由主义中的一种原教旨倾向而言,这其实并非胜利时刻,而是危险时刻。
本书认为,“诉诸自然”是新自由主义者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为应对所面临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的核心一环。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已死、但‘利维坦’仍在”的时代。即便资本主义成为唯一存活的经济制度,公共支出依然在扩张。
其背后是一个政治难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已将民权、女权、平权行动与生态意识这般被他们视为“毒药”的东西,注入了政治机体的血脉之中。政治正确与“受害者叙事”(victimology)的氛围使自由讨论窒息,并滋养了对政府的依赖与“特殊利益诉求”的文化。
新自由主义者需要一种“解药”。面对那些以牺牲效率、稳定与秩序为代价、持续不断的矫正不平等的诉求而困惑不已,他们在种族、智力、领土与货币等问题上转向“自然”,以此构筑一道壁垒,抵御进步派步步进逼的要求,并期望逆转社会变革,回到他们想象中植根于遗传与传统的性别、种族与文化差异的等级秩序。
正如斯洛博迪安所述,对于那些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战斗性信条而非宪制设计的人而言,苏联共产主义的战败不过是新一场战役的开端。而且从最早阶段起,生态与环境主义的观念就位于其中的核心位置。
正如斯洛博迪安所引《华尔街日报》1991年的说法: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的那个星期,全球领先的自由市场学者团体——朝圣山学社正在召开年会,这再合适不过了,……共产主义走下历史舞台后,对自由的主要威胁或许将来自一种乌托邦式的环境运动;和社会主义一样,它将人类福祉置于‘更高’的价值之下。”11
共产主义像只变色龙,正在把自己的底色从红色换成绿色。十年后,竞争性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弗雷德·史密斯在一次朝圣山学会社会议上警告说:“我们刚刚击退了一股红色浪潮,如今却有可能被一股绿色浪潮吞没。”他又说:“那些曾经打着经济进步主义旗号行进的力量,如今已在新的环保旗帜下重整旗鼓。”12
至少可以说,朝圣山学会这一派颇具先见之明。正是在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巴黎气候协定》双双出台,他们所设想的以正统的人权与环境主义价值为核心、重新编排权力格局的愿景抵达了顶点。
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头贴着新标签的新摩洛克(译者注:Moloch是古代迦南宗教中的神祇,与儿童祭祀有关,现常用于隐喻需要牺牲以维系的系统),诸如“公私合伙制”(PPP)与ESG等。
丹妮埃拉·加博尔(Daniela Gabor)早就把这一体制识别为一种新的“复合体”。它已不再是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而是以私人资本为中心的“华尔街共识”。诸如可持续发展目标之类的目标被誉为“普世价值”,净零排放被设定为长期目标;而整体框架——按照“发展融资”和“气候融资”的议程——则由全球公私合作与“混合融资”来界定。正如斯洛博迪安所指出的,这是一场在私人资本旗号下、面向人道主义全球目标、与公共行动协同却毫不避讳“逐利”的全球政策重塑(至少在修辞层面如此)。这正是他所谓“新自由主义式的解决方案主义(neoliberalism solutionism)”的最新一次升级。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切理解为去政治化的终极之举——在更为全面的基础上,对“历史的终结”作出的最后宣言。而斯洛博迪安精彩地展示了新右翼如何从内部对其发起动员。新右翼的本土主义与种族主义并非与新自由主义水火不容,而恰恰是从新自由主义内部孕育而出。
但若继续阅读2025 年 3 月美国外交官的声明,你会看到别的东西。继对气候与性别意识形态的谴责之后,出现了第二个转折:
我们同样担心,该决议标题中对‘和平共处’的提及可能会被挪用,用以暗示联合国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予以背书;而该原则并非经联合国认可的成员国谈判产物,也未通过联合国程序获得认可。
……同样,“文明对话”这一概念根植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该倡议试图通过重新界定“民主”、“人权”与“正义”等术语的基本含义——并扭曲此前载于《联合国宪章》等基础性文本中的既定定义——来为北京的治理体系及其人权侵害遮蔽批评,从而使其服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利益。”
此处所指之敌并非全球主义自由派精英,而是中国共产党。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似乎并未在斯洛博迪安所研究的那个激进圈层中产生显著影响——在文本中,“中国”仅出现了两次。正如他所指出的,他笔下这拨人曾被20世纪80年代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所撩动;也有人因亚洲群体在“钟形曲线”中的出众表现而担忧。
但要理解2015年“华尔街共识”的瓦解,尤其是美国权力为何从中叛离,我们无法将中国排除在视野之外。此举并非要转移斯洛博迪安笔下那群人提出的关于发展主义与普世价值的问题,而是要把这些问题置于另一种语境中加以审视。
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界定,不妨回到另一部影响深远的思想史著作:塞缪尔·莫恩(Sam Moyn)2010年的《最后的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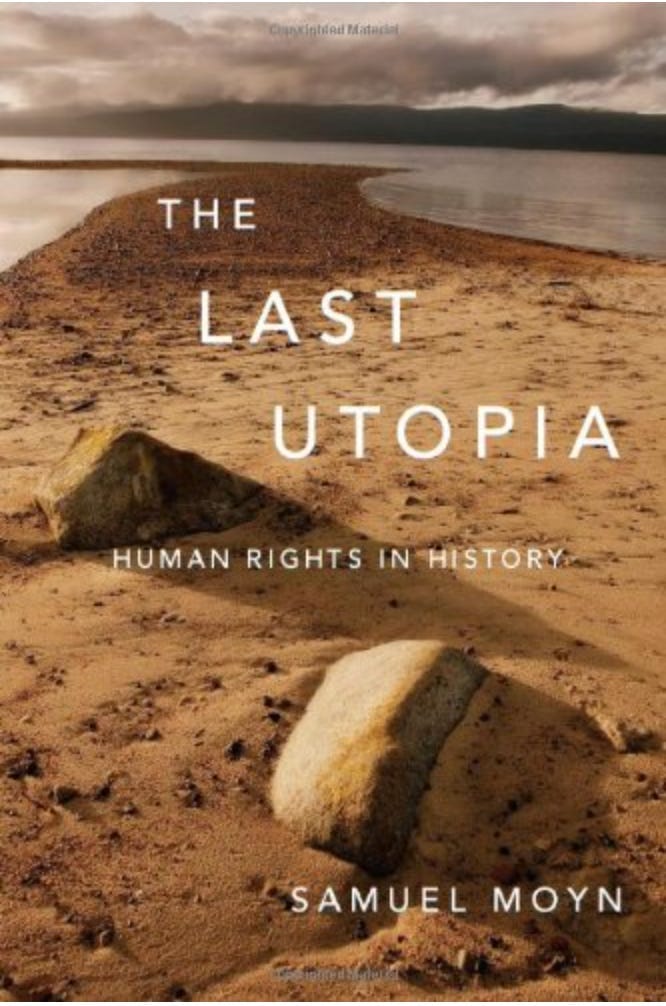
汲取马塞尔·戈谢等法国历史哲学家所提供的宏大叙事,塞缪尔·莫恩勾勒出这样一条轨迹:在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着后殖民发展及其国家主权承诺失去信誉,一种以普世人权法则统一世界的愿景开始兴起。冷战结束之后,普遍人权上升为国际事务的黄金标准,也与美国单极霸权的神圣化相伴而行。
因此,全球发展被重新定位在人权框架下——这正是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果——同时伴随着鲜明的去政治化,这绝非巧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发展问题”——这一在历史上与集体能动性和主权问题有机相连的议题——压缩为一套关键绩效指标(KPI)矩阵,这种简化可谓非同寻常。摆在台前的是蚊帐、初等教育与性别关系;而最初塑造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百年屈辱”和不平等条约,却无处可寻。
不得不承认,早在2015年,可持续发展已显得不合时宜。毕竟,那一年的全球“合流”发生在西方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冲突以及中东地区暴力升级之后,其结果是在欧洲引发了大规模移民潮与本土主义反弹。就在联合国会议上香槟塞此起彼落之时,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已在谈论“多重危机”。与此同时,2015年5月,北京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很快就在西方的集体认知中留下了第二次“中国冲击”的烙印。
正如我在一次为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所作的演讲中所论述的,回头看,2015年与其说是新篇章的开启,更像是最后的机会。因此,2016年的民粹主义反弹紧随其后,并不令人意外。
十年之后,正如我在《外交政策》上那篇颇具论战性的文章中所论述的,将“发展” 去政治化,仅仅理解为全面的人道主义改善与繁荣的愿景,已与现实完全脱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美国在抨击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所承认的,如今最大声维护2015年那套标准的力量是中国。北京手握诸多筹码,深知西方所能提供的寥寥无几。它已经在发展之战中取胜。把注意力集中在婴儿死亡率、饥饿和基础设施之类的议题上,使其得以压制有关公民自由的任何讨论。2021年,它推出了一套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物质层面相呼应的平行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作为一个深信历史站在自己一边的大国,它并不惧与全球发展主义议程交锋。与之相对,美国不再认为自己负担得起奢侈的“普世主义”。
我在此把斯洛博迪安所作的关于新自由主义右翼之思想动力的“内部”叙述,与关于美国霸权式微的更广角叙述区分开来,并非为了指出矛盾。二者相辅相成。哈耶克的私生子在美国霸权衰退所伴生的碎片化政治文化中,找到了大展拳脚与施加影响的广阔空间。但这种关系是或然的,是“充分而非必要”的。要理解这一点,不妨想想在特朗普1.0与特朗普2.0之间的拜登时期发生了什么。
拜登团队不遗余力地强调他们在恢复“常态”。他们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口头表示支持。在2021年格拉斯哥的首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他们推出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从南非起步。
JET-P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华尔街共识”融合的经典范例。但正如我在此前文章所论,它们也完全缺乏实质内容。
亚当·图兹:西方气候地缘政治的“纸老虎”——公正能源伙伴关系(JET-P)
另一方面,一谈到中国,拜登团队就划下了红线。他们加倍实施科技制裁,并搭建起全球性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在经济层面,他们思维的顶点是那句口号——“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这一设想旨在通过划定不可进入的直接对抗禁区与可进行友好竞争的区域,来调和大国之间竞争与经济发展的张力。但它非但没有缓解紧张,反而明确宣示了美国自居有权界定何为“可接受”的发展。更何况,偏偏是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把那些通常不会明说的话说了出来:只要中国“待在自己的车道里”,将自身增长轨迹限制在不挑战美国权力的范围内,就无需担心“修昔底德陷阱”或战争威胁。换言之,美国在开列自己的“和平条件”。
如果把2020年代视为新篇章的开启,那么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与斯洛博迪安和莫因各自叙述的起点之间的鲜明对照。
在20世纪70年代——莫因的起点——美国虽因越战失败与1973年石油危机而摇摇欲坠,但其回应是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到20世纪90年代——斯洛博迪安的起点——美国可以自称赢得了冷战。彼时,同样以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为号召的新保守主义,成为新的信条。与当下相比,反差尤为强烈。正如一位刚参加完第五届国家保守主义(NATCON5)大会的胆识过人的朋友告诉我的,他所目睹的几场主题演讲贯穿的唯一共同主线是:“美国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人民(people,原文如此)。它不是一种理想,也并非一个理念。”